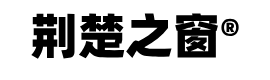罗田县城的东门,旧时有一座木桥,窄得只容得下一人而过。桥板间的缝隙,大得可以漏下小儿的脚,每每行走其上,便如履薄冰,战战兢兢。河水在脚下奔流,桥身在风中摇曳,行人只得眼盯桥面慢步行走,生怕一个不慎,落入河水中。改革开放后,当地村民自筹资金,建木桥,每逢洪水季节将桥板抬到岸上,防洪水冲走。洪水退后,又铺上桥板,并收过桥费。价钱不高,由原来每趟5分,后来最高收到每趟5角钱。

我老家在大河岸镇,少年时进县城,多次走过那桥。彼时的木板已显出几分朽态,踏上去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桥头常蹲着几个卖菜的人,菜叶上还沾着晨露。他们蹲踞如蛙,眼睛却亮得很,盯着往来行人的脚步,仿佛能从那迟疑或果决的步伐中,窥见买主的心思。
“走稳些!”他们有时会突然吆喝一声,不知是提醒顾客,还是警告那摇摇欲坠的老桥。
2002年,听说要建新桥,县城东门一带居民,喜形于色。县委、县政府号召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捐资建西门和东门大桥。时任县交通局副局长郑耿负责建设,带人测量,请华中科技大学设计院设计;时任公路段路桥工程处主任的宋佑明,中标领了这施工差事。两年光景,一座水泥大桥横跨在义水河上。大桥长189米、宽12.5米,双向两车道,汽车可以并排而过。通车之日,附近的人,扶老携幼来看热闹,桥上桥下挤得水泄不通。小贩们也趁机兜售糖人、气球,孩子们尖叫着在人群中穿梭,险些酿出乱子。
东门大桥初建时,确也风光了一阵。然而不过十余年,车辆渐多,桥面又显得窄了。上下班时分,汽车排成长龙,司机们不耐烦地按着喇叭,声音在河面上传得老远。骑自行车的、骑摩托车的,便在车缝中钻来钻去,险象环生。
2016年底,县委、县政府又有了扩建之议,并更名为巴源大桥。还是那郑耿,如今已任县交通局长;还是宋佑明,已升了公路局副局长,兼县交通投资公司的经理,又是公路桥梁一级建造师,领回巴源大桥改扩建任务。大别山路桥公司中标承建,2017开工,机械轰鸣了一年,新桥便横跨在义水河上,宽度翻了一倍,双向四车道,人行道竟有四米之阔。是县城七座桥中,桥面和人行道最宽的桥梁。

新桥通车那日,我去看了。桥面平坦,路灯杆锃亮,不锈钢栏杆上的花纹是新式的,说不清像云还是像浪。许多人在桥上走来走去,有的特意来回多走几遍,只为体验这宽阔平稳。几个老者站在桥中央,指着河水说古:“从前发大水时,旧木桥如何被冲得无影无踪,又如何在下游十里处找到几块残板。这桥可冲不垮喽!”他们摸着栏杆,笑得露出了残缺的牙齿。

桥北是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,桥南通人民医院,这位置选得极好。每日清晨,学生们如潮水般涌过桥去;黄昏时分,又退潮般返回。救护车偶尔呼啸而过,桥上车辆便默契地让出一条路来。生命的两端,竟被这一桥连接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夏夜的巴源大桥成了纳凉胜地。路灯亮起来,桥面上便聚集了各色人群。唱歌的,支起话筒,声音混着电流的杂音,刺耳却热闹;下棋的蹲在地上,棋子拍得啪啪响;情侣们倚着栏杆,影子在灯光下交叠。小贩推着冰棍车穿行其间,吆喝声淹没在嘈杂中,只看见他们嘴唇的开合。
我有时也去桥上走走。四米宽的人行道,竟也显得拥挤。一群老人围坐一起,打扑克,旁边放着茶缸,不时饮上一口;几个少年踩着滑板,从人缝中穿过,引来一阵骂声;婴儿车停在一旁,里面的婴孩睁大眼睛,望着头顶的灯光出神。
最热闹处,总有几个文艺爱好者,一个拉二胡的老爷子,一个吹笛子的小伙子,还有唱歌的姐妹,日日定时出现在桥的东侧。拉《二泉映月》、《赛马》等名曲,琴声上空回荡。有人驻足听上一段,有人匆匆而过,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还有唱京剧一伙人,唱黄梅戏一族人,好似比赛,纷纷唱入迷;还有说鼓书的不甘示弱,鼓点敲出了节凑感,声音揉在杂音中。桥上拍抖音的,争先恐后地抢拍,这桥成了网红桥。盛夏的晚上,还有警察上桥维持秩序。

桥下的义水河,千百年来就这样流着。它见过木桥的腐朽,见过水泥桥的兴建,见过无数双脚从它上面踏过。河水不会记得每一个过客,而桥却承载了太多记忆。
如今的巴源大桥,成了县城的一处景点。年轻人来这里拍照打卡,背景是霓虹般的桥灯;老人们来这里回忆往昔,话题总是当年那独木桥变为四车道水泥桥,是罗田的幸福桥,致富桥。它见证了罗田在党的领导下山城巨变,折射出罗田发展的日新月异。是啊,桥新了,可人老了!
偶尔夜深人静时,我站在桥上,想起巴源大桥的前世今生,看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,恍惚间又听见旧木桥的吱呀声。那声音微弱却固执,仿佛在提醒人们:所有的坚固都会腐朽,所有的宽阔都将拥挤,所有的记忆终将模糊。桥如是,人亦如是。
原创文章,作者:荆楚之窗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jingchucn.com/14535/